當人以死亡做為根部
人就突然地安定下來
開始對自己有限的生命一有一分珍惜
甚至產生一種了斷的感覺
只有站在這種情況下去活
才是比較真誠的活。
死亡對每個人絕不是假設,更不是理論,而是無人可以逃避的事實。這原本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但是我們卻不曾真正認識這必然的命運在每人的身上會出現什麼景觀。一旦我們避問這「生死大事」,或不正視大限的必然性,我們就會像孤魂野鬼一樣,成天東飄西盪,找不到自己的根。
我們的生命史裡,其實是由一連串「進」、「出」所完成的,我們經歷過「入學」與「畢業」,我們找到新的工作,離開工作退休;我們結婚、離婚;我們戀愛與分手;而最大的「生死大事」則是終極的「進」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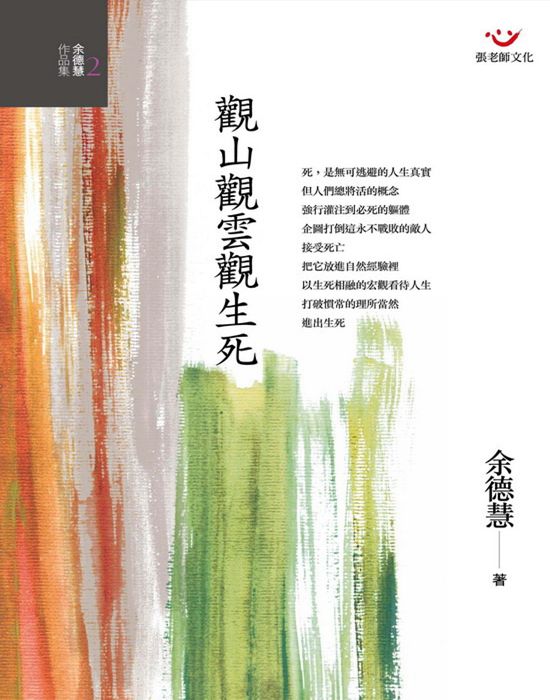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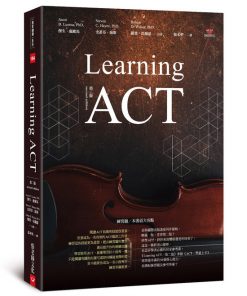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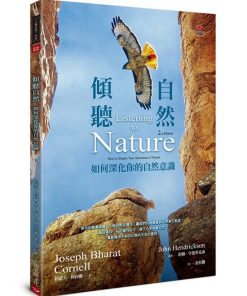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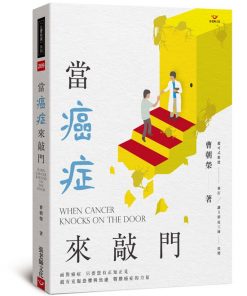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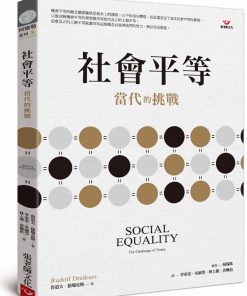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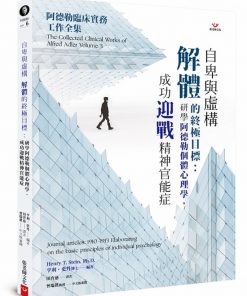

商品留言
目前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