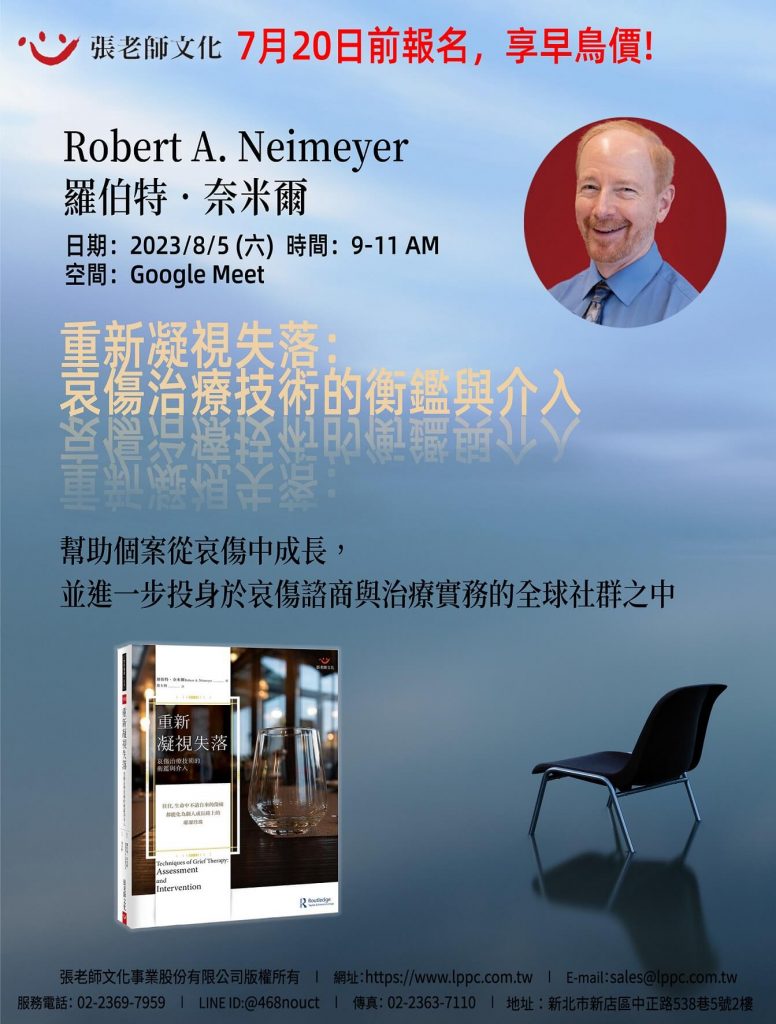疾病與傷痛永遠不請自來,
沒有人的生命能避免失落,但失去並不是終點。
從吳嫣琳的回憶開始,想像和悲傷同行後的成長。
撰文/黃曼茹 (摘錄至《張老師月刊》2020年6月號第510期)
照片提供/張老師基金會
純色的牆壁、淨白的制服、無機質的醫療器材以及不自然的藥味……很多人一想到醫院,首先憶起的便是遠離外在花花世界、缺乏生機的景象,彷若空間本身就足以代表重症病人住在其中的心境:不得不接受自己的身體失去了某種功能、流失了某種活力,只得仰賴儀器與藥物,掙扎著度過餘生。假若美好的過往已不復返,人生難道只剩下獨自等待凋零的選擇嗎?我們似乎很少想像,即便來日不多,依然會有人走進你的病房,陪在你身旁,聽你講述自己的故事,發現人生這條路走到此處,其實早已留下夠多寶藏在你心裡,任何變故都無法抹滅那些光輝與意義──曾任新加坡兒童癌症基金會首席輔導員,長年致力於癌症安寧療護、臨終和喪親輔導的吳嫣琳,便和許多病患一起走過最後一段時光。讓我們也從她的助人回憶開始,想像和失落、悲傷同行後的淚水與成長。
難以承受的疾病當口
中文都說「生老病死」,好似人老了之後才會面臨疾病和死亡,但吳嫣琳卻輔導過許多罹癌的兒童與青少年。不分男女老幼,癌症帶來的衝擊一樣巨大,但對這些彷若剛冒芽便要凋謝的孩子而言,更像是來不及後悔人生,就先被剝奪了所有的可能性。明明該在藍天白雲下,和同儕一起嬉戲並追尋夢想,場景卻驟然換成了白色的天花板,以及僅能從窗戶看出去的天空──這就是吳嫣琳曾輔導過的一位少年,原本他是足球校隊的隊長,擁有矯健的雙腿、隊友的簇擁以及熱血的求勝心,但當吳嫣琳認識他時,他面臨的已經不是同樣青春的對手,而是癌症末期的困境了。吳嫣琳提到,不同於幼兒,青少年階段已經能了解疾病帶來的威脅,對人生也有自主意識,醫護人員當然希望能聽到病患親自說出期盼的照顧方式,才知道什麼是最好的安排。然而進到實際療程時,不是每個個案都準備好談這些事,尤其是急救這類攸關生死的重大問題,個案必須去設想最壞的情況:自己最無力、最危急,可能也是最絕望的時刻,這更是難以承受的負荷。
因此吳嫣琳請這名少年按照他熟悉的球賽處境,以他隊長的身分,畫出現在的局勢、攻擊和守備的策略,以及這場比賽中兩隊不同的隊友與教練。透過繪畫,不僅幫助少年的父母和醫療團隊理解少年對疾病與治療的看法,更讓少年找回自我的掌控感並感受到重要他人的存在。「我用這種隱喻的方式和他談這些事,最重要的原因在於:即便他處在病痛中,身體每天都在衰退,現實中也不可能再上場比賽了,但他還是可以守護自己作為一名足球員的身分,持守他的性格與價值觀,並從中應用自己所擁有的能力和過往累積的經驗,來完成他生命中最後一場『球賽』。」
於最委頓處創造生機
這張「球賽戰略圖」,同時對少年的父母意義非凡。因為病患會難以啟齒,除了受限於自身壓力,往往也有想體諒親屬心情的顧慮。當少年能以足球隊長的姿態,侃侃而談癌症這個對手,父母便能看到他不同於其他孩子或病人的一面,有機會開啟親子間更深層的對話。
吳嫣琳提到,她的角色不只有扶持傷痛的心,也包含引導或疏通親子關係,「在可能喪子的危機前,父母其實很需要被孩子肯定。」如同戰略圖,吳嫣琳也會安排親子互相說一些話,或為對方做點事情(如手工藝),將「能為孩子盡力」這件事具象化,讓因孩子的病情感到無助的父母,重新體認到作為父母的意義:「正因不是每個家庭都能自然地交心,他們就更需要我們藉由不同的形式,促進父母和孩子間的溝通與連結,更深地互相理解,說出平常可能沒表達的話,這一切都能在病痛和悲慟中,製造很美好的回憶和安慰。」
少年的病情復發很多次,癌細胞已轉移至多處,不論他自身、家屬還是醫療團隊,都理解他在可預期的未來會離開人世。對少年的父母來說,他們無力挽救註定的現實,但這些回憶就能在將來,成為父母重新站穩的立足點,讓他們回顧過往的照護歷程時,知曉自己已經盡力了,在這段短暫的親子緣分中,盡其所能地把握住最後相處的時刻,沒有留下遺憾。
陪伴他人之苦痛
在少年的癌症足球賽中,他將吳嫣琳視作教練,因她能從更全面的視角,提點少年在面對癌症、父母時,自身真正在乎的事物。吳嫣琳對此當然感激,但比起被稱作教練,她更喜歡稱自己為個案的「同行者」:「助人工作者也是人,今天個案身上的遭遇,若發生在我身上,我可能也有相同的掙扎。我不會將自己視作權威來告訴個案該怎麼生活,因為個案會有他自己的智慧,他和我平等。我能做的是在個案被情緒、壓力籠罩時,幫忙撥開這層霧,看清前方的道路──陪伴他,讓他在困境中不感到孤單,我覺得這就是助人工作者能給予個案最大的支持。」
吳嫣琳提到,陪伴癌症個案,便是和他一起經歷不斷失落的旅程。起初個案失去了可見的身體機能,再來失去了心理的價值或信念,更多時候是兩者交織在一起,成為旁人無法理解的複雜感受。比如個案因化療掉髮,身邊的人雖然都知道他失去頭髮,卻不見得能體會失去頭髮後對自我形象的打擊。所以,比起慣稱的「哀傷治療」、「悲傷輔導」等用語,吳嫣琳實際面對個案時,更強調失落的重要性,「未必是悲傷,也可能是憤怒、怨懟,覺得上天很不公平──我們要先知道『他失去什麼』?失去的事物,對他來說有什麼功能或意義?為何對他如此重要?這樣比較能同理他的處境。」藉此平撫個案的情緒是理由之一,但更深層的目標,是要幫助個案重新建立人生意義。
「失落其實是一體兩面,當然要看到失落帶來的負面衝擊,但不能忘記還有另一面:失落也彰顯了個案想守護的事物。」好比上述提到的頭髮,如果在個案心中代表了自我形象,助人工作者就可以陪個案一起釐清「他重視的形象究竟是什麼?」進而找到不需依靠頭髮,也能重建形象的方法。「幫助個案看到正反兩個面向,他較不會陷入全然絕望的處境,能通過不同儀式、活動,來鞏固他所珍惜的關係,或繼續扮演他心中理想的角色。」
分離、創傷、死亡……沒有人的生命能避免失落,但失去往往不是終點,而是學習用另一種方式,充實過生活的起點。看完吳嫣琳的助人故事,我們彷若也「同行」了一遭他人的失落,一起詰問生命的價值。不論讀到此處的你,正安穩順遂,還是歷經風浪,都邀請你從此開始,進到哀傷治療的世界,期盼終有一日能推開所愛之人或自己的心門,找出失落的意義。
吳嫣琳
新加坡兒童癌症基金會首席輔導員,專職於癌症安寧療護、臨終和喪親輔導。現任美國波特蘭失落與變遷研究學院副總監。不僅擁有多年輔導個案經驗,亦在各國培訓、督導助人工作者。